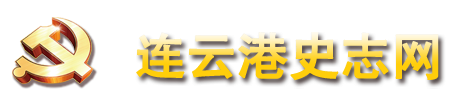莫延安
打小我记事,咱们乡下每家每户的大门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放着两块石礅,那些石礅硕大而平整,可供人们歇息消闲之用,美其名曰:“歇脚石”,单听这名儿,就够温馨动人的了。
一块块原本冷冰冰、毫无生气的石头,一旦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愿望,便有了它们鲜活的内容和十足的人情味。我无从考证这一民俗的由来,只能设想种种可能,并引发开去,用心揣摩人们创意时的初衷。可以想象很久以前有位先人热情好客,有一天突发奇想,在自家大门旁放置了两块石礅,供过路的人歇脚……也许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我设想的这么浪漫,这么尽善尽美,人们在门旁放两块石礅,只不过是图自个方便,或者仅仅是为了缓解雨水对墙基的冲刷而已。但当这一习俗逐渐被人们所认可、效仿,加以完善,能坦然地将自己劳动创造的美和快乐与他人一起分享,歇脚石,已成了民间一道乡情浓郁、独具特色的风景。
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山村,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一旦空闲下来都习惯坐在门前消遣,夏日纳凉,冬日晒太阳。大老爷们往往是大大咧咧地朝歇脚石上一坐,翘起二郎腿,衔着烟袋,或点上支自卷的纸烟,吞云吐雾一番,三五成群再山南海北旁若无人一通侃。婆娘们则斯文多了,她们多是拿条凳子或拎个蒲团聚在一起唠嗑,手里很少闲着,绣绣花,搓搓麻绳,纳纳鞋底,不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。不知是顾及形象,还是另有原因,婆娘们很少坐到歇脚石上,歇脚石似乎成了大老爷们的专座。
那时我们家的歇脚石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品,每天放学回家,我常常把歇脚石当作课桌,趴在上面边做作业,边等妈妈收工回来。有时等门等得太久,我便偎在上面打个盹,每每妈妈把我叫醒,总会心疼地亲亲我的小脸蛋,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多年以后,当我正襟危坐在大学的课堂里,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门口那块陪伴我度过整个少年时光的歇脚石。
有时歇脚石也会接纳一些不速之客,他们多是唱门的艺人,尽管他们和叫花子一样落魄,但他们同叫花子有着本质的区别,他们是凭吹拉弹唱的手艺挣饭吃,不像叫花子那么露骨地乞讨。唱门的艺人每到一家门口,决不像如今那些到处横冲直撞张口就要钱的无赖乞丐,他们总是很规矩地站在门旁的歇脚石边,自弹自唱上一段琴书或吕剧,直唱得人家过意不去,动了恻隐之心,施舍点吃食,他们再连声答谢后转身离去,从不争多嫌少。对于他们我从来没有任何鄙视,有的只是同情和虔诚的祝福,但愿他们都能早日摆脱窘况,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,真心希望下一块歇脚石就是他们乞讨之路的终点,从此不再浪迹天涯,真正拥有一块名符其实的歇脚石,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
如今,走街串巷的唱门人已很少见到了,歇脚石也倍受冷落,难登大雅之堂,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尊把门的石狮子,威风凛凛,令人望而却步。关门闭户的现代人,再也无缘身临其境,去体验歇脚石的温存,那些颇具乡土气息和人情味的歇脚石,已成了人们心底的一个情结。有关歇脚石的传说,就像夏夜的萤火,若隐若现,但却温暖人心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