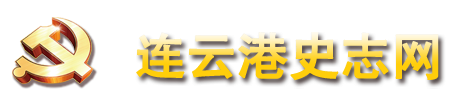乡间书场
高传胜
在我记忆的海洋里,要数那童年时代东海的乡间书场印象最深。
那时的说书艺人所至的街头巷尾无不留下一串串欢声笑语,那是偏僻荒凉的小山村一道极佳风景:茶余饭后的黄金时间,一通鼓响,乡民们来不及揩干嘴角糊粥,便兴致勃勃地倾巢而至,团团围坐得风雨不透。有月的夜晚,月光迷离,暗生幽情正可入戏;无月的晚上点一灯如豆,更多了飘思冥想。那巧舌如簧的说书艺人,鼓点响起,三尺地面可作舞台,呼风唤雨,战马奔腾,刀光剑影,说得你如临其境。真是说尽前朝兴亡事,渗透人间悲欢情。说者眉飞色舞,听者如醉如痴,更有那心软的妇人听至伤心处不约而同地落下几滴同情的眼泪。那时的说书艺人十分吃香,常可以在一个村上说上个把月不离窝,且有那村民供吃管喝,还有那德高望重的庄上人领门带户凑份子给他辛苦费。
那时附近几村说书最好,能让人神魂颠倒的要数俺那近房长辈三爷了,他举止儒雅,说起书来抑扬顿挫、婉转流畅、出口成章,使人入耳难忘。一部《杨家将》竟能连续说上个把月,我真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,娴熟的演技。一回三爷在一村说书有数月,尽知腹中之书已被书迷们扒尽,便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村,行至村头路旁见一堆牛粪被屎壳螂盗得破烂不堪,顿时灵感倾来,随即编了一部《大破牛屎山》,又回那庄说得有鼻子有眼,把村民们乐得前仰后合。这件事被我族上人传为佳话。
现在乡间书场已成了记忆中的事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丰富多彩的影视节目及现代音乐,尽管如此,我却永远眷恋那浓浓的乡音乡情。
别了,说书艺人,
别了,乡间书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