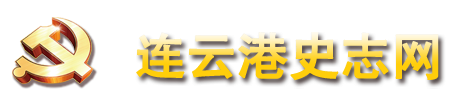姜威
作为“外乡人”,到连云港这“落头”来工作,“离啦”四五十个年头了。加引号的几个词,是从海州话里听到的,如将它们直白为“外地人”、“地方”、“经历”,顺倒是很顺,只是没了海州味儿。
常言“入乡随俗”,在来连云港市(那会叫新海连市)之前,一位连云港籍的领导关心地对我讲:各地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,那也是一种风俗,可别听到不顺耳的话讥讥笑笑,那样会“恼人”的。如果听不懂,那就作点调查,下些功夫研究研究吧。来到港城第一天,便遭遇到不懂方言。
那是下车伊始晕头转向的时候,我走到车站前面的解放路边,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向我兜售“五香鸡蛋”,便趁机相询:“请问小姑娘,到新海中学去,是从这条大路朝前走吗?”姑娘顿时笑容盈盈,关注地望着我,说了声:“爱么!”啥?啥?素不相识的,怎能如此轻率,突然间探问一个生人爱不爱她呢?可笑可笑。
后来才知想岔了,可笑的是自己。什么爱不爱的,那是“哎幺”——含有肯定语气的海州口语,如同“是的”、“对啦”。在教书的日子里,我要求学生说好普通话,学生照做了,可那海州乡亲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口语“倔强”得很,还是时不时地从学生的口中“吐”将出来。一天,两个调皮的学生在一起吵嘴,被我喝到跟前,先问甲:“说说,为什么要吵?”他把脖子一梗,忿忿地指乙道:“他——嚼蛆!”
什么什么,“绝曲”?我不懂该词,乍乍的心作“间译”,但仍迷迷茫茫。
事后明白了,“嚼蛆”之说类乎指斥别人“胡说”、“造谣”。想想挺有道理,嘴巴里头嚼着蛆,多脏呵,能不引起强烈的反感?形象、生动,贬义浓而又奇,实在是妙!
日子一长,对流行的海州话也就耳熟能详,不觉奇怪,经琢磨和“研究”也能大体上知其所以然了。比方说:“倒头鬼” ——是对某人不正确的做法表示不满的责备;“促寿” ——大约是“缩寿”,为人缺德或言行下作,自然会挨此一骂;“拉村” ——联系语言环境,知是“讲下流话”;“怎置” ——不是指东西怎么放,而是“怎么办”、“怎能这样”之类的俗说;“殃根”――祸害;“顺溜” ——顺利;“磨牙” ——吵架;“出鬼” ——蹊跷;“有虚头” ——不实在;“该败的” ——不像话;“不归功” ——不行,没好结果;“冷货” ——不好卖的东西;“巴巴” ——常常,往往;“撩骚” ——故意恶作剧,计人嫌……
至于整头整脑的海州话,所闻也多。“先生啦,来家蹲蹲”,“需着尽管说”,“吃点亏,在一堆”,“请问贵姓,免贵免贵,贱姓×”,“小马要操,小鸠(小孩)要教”,“瓜香甜不分老嫩,人品好不在丑俊”,“改错如洗澡,人正鬼吓跑”,“做大(老)不正,拉来垫腚”……
如此这般不胜枚举,构成一方民间的语俗。据知,在探讨《镜花缘》出处的时候,有学者从这部名著中理出许多“海州话”,一经此证,铁板钉钉,谁也无从置否了。
如今海州话渐趋淡化,兴起标准口语。如此也好,咱们港城开放了,普通话迎客,文明形象自会高上一层。